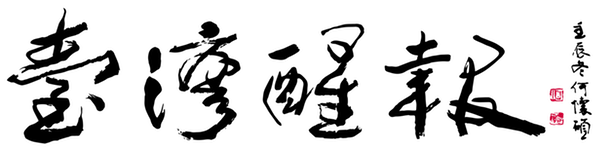重讀林義雄滅門血案,那怕相隔46年,還是讓人潸然淚下,慈母幼女滅門式宰殺,成為台灣民主發展上,永遠的殤與痛。
那是永難癒合的傷口,不忍卒賭,因為遲遲不見真相。萬萬沒想到,影劇圈嘻皮笑鬧式的重啓話題,揭開陳舊疤痕,血已流乾,痕已乾涸,但老疤重撕,痛楚加劇。
屈指一算,可愛的雙胞胎姐妹,如果還在世,如今應該年過半百,是有為的女史,然而,她們面前血案,她們來不及長大,長眠在至愛的阿嬤身邊。看著他當年的全家福照片,小女孩的純真可愛,老母親的慈眉善目,直叫人痛徹心扉。
悲劇拍成電影
悲劇事件拍成電影,不僅僅是痛苦的再現,更是事實的還原,心靈與美學的提升。藝術讓悲劇,不再只是「失去」,而成為一種「有意義的痛苦」,透過「情感淨化」、「形式賦予」與「主體覺醒」,將生命中難以消解的磨難,轉變為具有永恆價值的審美對象。
近年打著還原歷史真相,搬上電影銀幕的案例很多,也有不少出色作品。基本上,倘若要將該悲劇拍成電影,通常需具備以下關鍵要素與考量:
一、家屬同意與尊重:
由於林義雄先生及其長女林奐均仍在世,且傷痛真實且深刻,取得家屬信任與授權,是倫理上的第一要務,否則將面臨社會抵制。
二、真實呈現歷史暴力:
《林宅血案》,是被促轉會定調為「國家機器」介入的歷史慘案。電影應深入揭露戒嚴時期情治單位監控、壓迫的真實情境,而非僅是懸疑辦案。
三、避免成為嗜血的商品:
該案充滿黑暗、人性泯滅的色彩,拍攝重點若錯誤放在「殺人過程」或「懸疑感」,會被形容為「拿饅頭沾血吃」,缺乏對受難者的同理心。
四、釐清導演與製片背景:
若創作團隊與當年的警備總部(涉案方)有淵源,如《世紀血案》導演背景遭質疑,極易引發替加害者「洗白」的質疑。
五、藝術與轉型正義:
成功的改編,應如《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1987: When the Day Comes),那是一部2017年12月27日上映的韓國電影,比較嚴肅朝向反映歷史真相、警示未來而努力,而不僅是為了娛樂或搶奪詮釋權。
林義雄的悲劇是台灣歷史上的一道血色傷痕,若要影像化,必須要有極高的倫理自覺與歷史責任感,避免將這起駭人聽聞的滅門事件輕率化。
從痛苦中昇華
反觀古今中外,悲劇事件轉繹為藝術作品,不在少數,理論核心,包括:
一、從痛苦到昇華
1、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B.C.)的「淨化」 (Catharsis):
在其著作《詩學》中提到,悲劇透過激發觀眾的「憐憫」與「恐懼」,使這些負面情緒得到宣洩與過濾,最終達到心靈的平衡與平靜。
2、尼采(Nietzsche,1844-1900)的「酒神精神」: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主張,藝術是受苦者的救贖。悲劇英雄勇於面對生命的恐怖與不確定性,並在自我毀滅中肯定生命的無窮創造力,將痛苦「神化」為一種極樂。
3、黑格爾(Hegel,1770-1831)的「辯證衝突」:
認為悲劇反映了人類生活中必然的倫理衝突,透過個人的倒下達成精神上的更高和解與秩序。
二、轉化的機制
1、形式的掌控:
藝術家將混亂的創傷,轉化為有組織的敘事或意象。心理學研究指出,透過這種「重寫生命故事」的過程,人從受害者,轉變為主動的創作者,重拾對生命掌控感。
2、距離感的建立:
悲劇藝術讓我們在「安全距離」下體驗極端情緒。這種「虛擬體驗」不僅提升了對痛苦的耐受力(如刺激腦內啡分泌),也讓我們能客觀思考人性的本質。
三、經典藝術實踐
1、繪畫方面,畢卡索(Pablo Picasso;1881-1973)的《格爾尼卡》(Guernica)把戰爭的殘酷,轉化為震撼世界的立體主義符號。孟克(Edvard Munch,1863-1944)的作品如《吶喊》(The Scream, 1893),或是充滿死亡氣息的《病中的孩子》(The Sick Child, 1885-86)。將他自幼喪親的憂鬱與精神焦慮轉化為極具渲染力的色彩與扭曲線條。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在情人自殺後,創作的《三聯畫》,生動地捕捉了生肉般的痛苦與掙扎。
2、文學與戲劇: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的4大悲劇(《哈姆雷特》、《馬克白》等)透過角色的道德困境,展現了人類在命運面前的尊嚴與脆弱。台灣228事件等歷史集體創傷,在陳澄波(1895-1947)等藝術家的遺作,被重新挖掘後,轉化為臺灣美術史中重要的歷史見證與反思。
回首台灣的歷史可真是一步一腳印,所有民主自由、轉型正義,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對於付出血淚與生命的台灣前輩與家人,致上最高敬意。我們樂見文學、藝術與電影的轉繹與重現,但應該本諸人性,將心比心,歷史不能遺忘,真理不能扭曲,前人的血與淚,更不能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