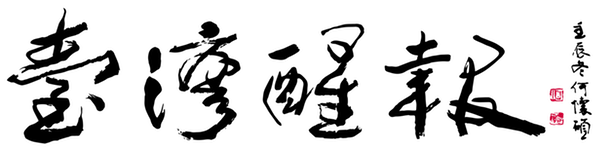上一節我們揭示,在「口傳妥拉」的大概念下,最早的猶太基督徒不會設想「公開出版」或對外流通這份(或多份)他們手上共筆性質的Q;它也當然不會寫在(正規出版品格式的)卷軸上。Q為何沒有在歷史記述中被公開提及過、也沒有殘篇出土,但同領域學者卻幾乎一致認定這樣的筆記存在?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我們透過瞭解Q筆記簿最初的可能型式來分析這個問題,也就是耶穌談道的筆記最早可能是寫在「木蠟板」上的。
圖一:古代的木蠟板(Photo by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頁冊的前身是木蠟板(wax tablet; tabula cerata)、木簡(wood leaf tablet; pinax),以及羊皮紙記事簿(parchment notebook; pugillares membrane [membrana])。(註1)前者是以成對的長方木板,中間挖槽灌蠟(想像一座注水的游泳池,或見上圖一),以便古代的硬鋼筆(stylus;鐵針)在上刻寫,寫完闔上木蠟板,對文本進行保護。木蠟板是可以反覆書寫的筆記本:只要平板上已書寫的蠟刮除後重灌鋪蠟,就可使用如新。
古代筆記簿的優缺點
我們現在出土的2000前羅馬時期這種原始的平板筆記本,板上的蠟早已揮散光了,但有趣的是,當硬鋼筆穿透薄薄一層蠟後刻蝕在木板上「入木三分」(見上圖一),卻可供古文歷史學者識別究竟前人用這類筆記本寫些什麼。那麼,既然硬鋼筆可以直接書寫在木片上,另一種筆記本的型式就是薄木片穿孔裝訂成的木簡(想像手風琴的活動簧片拉開及闔上的樣貌,或見下圖二三)。

圖二:古代的木簡(Photo by Wikimedia)
圖三:古代的木簡(Photo by British Library Blogs)
木蠟版的缺點是「字跡和頁面沒有顏色對比」所以不好閱讀;木簡若不用墨則刻上去的對比度更差,而且木纖維的表面刻寫起來相較費勁。羊皮紙薄且柔軟,但製作工序複雜、做成卷軸比較常見,當成筆記本至少是知識階層以上的選項。
木蠟板最可行
耶穌的話最早的版本記錄寫在木蠟板上的機會最高,這乃是從經濟階層、人體工學、傳統選項而來的加權研判:
1) 古羅馬基本上沒有「書桌」,要到皇帝的書記官或是富豪大戶家才會有案几(形狀如茶几或板凳)、畫架,可以鋪紙和擺放墨盒。
2) 由於沒有桌子,絕大多數的文士或是聽道的學徒,必須都站著或坐著在大腿上抄寫東西,軟性的「羊皮紙」和跟「莎草紙」都不適合在沒有「墊板」、非硬質平坦的表面上書寫。
3) 硬質「木簡」的筆記雖然能提供「墊板」功能,但木簡與紙一樣沾墨水才能寫字,且木質表面的讀寫體感又遜色,不利聽寫摘要速記(想像一下在樹皮上面「刻字」與在紙上頭「寫字」的對比)。
在沒有空間和時間餘裕沾墨、擺桌,跟著耶穌佈道而移動的門徒,只有使用成本低、具墊板功能、表面又相對柔順好寫的木蠟板,就是唯一適合。(註2)
然而這也是最不利文字保存的一種格式。Q具體消失為何?聖經學者咸認為原因是在馬太福音/路加福音誕生後它作為成文文獻「物盡其用」,信徒絕少再有動機抄寫和傳播這份文件。
而我們從新媒體的格式和載體去分析,更強化了這個推斷:正如前面提過;「米示拿」的希伯來文意思是「複習」。如果 Q的文本由來最可能是源自耶穌講論抄寫下的木蠟板,那麼即便這份共筆未來被翻譯、擴增、轉寫、合併到其他類型的筆記本上,它也難免繼續被視作一份素材、一份輔助福音口傳、信徒崇拜聚會或日常實踐的「手冊」(handbook/manuel);除非格式歷經蛻變,否則自然不會有出版典藏的地位。
(如同即使傳聞中抄得極其精美,幫助無數人度過考試的某醫學院課程傳奇共筆,也不會有 ISBN出版號;有別於正式出版品,絕大部分人在網路上搜尋不到,也不會見過。)
用身教成全律法
過去「確信有Q、卻一輩子沒有機會目睹Q」的學者,難免有些報憾失落;「道成肉身」的耶穌既不是選擇投胎帝王將相世家,而是加利利漁村的木匠家,我們也難免承受這樣的學術「苦果」:即基督永活之道,乃是由不特別學問出色的三教九流門生記錄在那些廉價、不起眼,浮蠟不堪歲月浸蝕風化的木蠟板上。(註3)
這必然也是一位馬槽降生、降卑為人的「神」預見並選擇承擔的物理限制:耶穌來,並沒有帶下一部高級、神聖、永恆的「卷軸」聖言(成文妥拉),而是按著2000年前猶太夫子「口傳妥拉」的精神,用生命和身教「成全了律法」。
然而,與同期拉比猶太文士傳統將「口傳/成文」律法嚴守二分不同的是,這個我們所知的木蠟板筆記階段也充分催生了接續的基督徒揚棄卷軸、將「耶穌教導/上帝啟示的新約」轉寫在莎草紙頁冊——由木蠟板筆記進化成的「新媒體出版品」——的動機,從而在未來釋放出這項「新媒體」的巨大優勢。(註4)
催生福音普及
初代基督徒明白至尊的神、至聖之道的自我啟示,並不拘泥於人間型式的理想和貴冑繁文縟節,他們所衍生的實踐也與他們從耶穌領受的神學信念合而為一:以「口白」俗文載道、以「頁冊」筆記出版福音見證,帶出早期基督教推倒社會高牆的階級扁平化和「福音」普及化的傳播爆炸。
這恐怕就是謎蹤般「輕輕地來,又輕輕地走」的Q本生命歷程,所要啟發的新媒體神學意涵。
亦如使徒保羅所說:「你們是基督的書信,由我們所經手;不是用墨寫的,而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不是刻在石版上,而是刻在人的心版上。」(哥林多後書 3:3)這福音比起能刻在不朽的石版上,更在意要寫在人的心版上。
註:
- 1. 此乃基於它們共同具有「翻頁(開闔)」的型式,對比卷軸的「滾/捲」型式。我們可以發現,當今數位時代的屏幕或移動裝置閱讀,又「復古」回頭採納卷軸的滾動滑屏設計。
- 2. 註5引用的李伯曼出處,從拉比文獻指出門徒在pinakes(Πίνακες)上寫筆記時,係將該詞誤解為「莎草紙平板(papyrus tablet)」,造成後續引用其觀點的學者在「頁冊」起源的探討一度迂迴。如今這個希臘古字乃是羅馬時的木簡(wood leaf tablet),蓋無疑意。此處呈現的也是學術去蕪存菁的鑑別成果,特此說明。參 Colette Sirat (1985). “Le livre hébreu dans les premiers siècles de notre ère : le témoignage des textes », in Calames et Cahiers, Mélanges de codicologie et paléographie offerts à L. Gilissen, éd. J. Lemaire et E. Van Balberghe, Bruxelles, p.169-176. 以及 Graham N. Stanton (2004), p. 187 的歸納。
- 3. 克洛普堡(John S. Kloppenborg)在The Formation of Q (Fortress 1987, p.81) 另猜測,也被併入馬太福音的「馬可福音」,能夠沒有淪為像Q一樣消失在歷史洪流中的命運,只是因為「剛巧」馬可福音被基督徒帶到了莎草紙盛產的埃及。然而這個理由忽略了新約四福音書都是作為「大眾出版品」的樣貌面世;反之,整份q傳統的定性,縱使歷經30餘年的擴充、翻譯——緣起於公元30年代門徒聽講時抄寫耶穌教導的「(亞蘭文)木蠟板」,到或許於公元60年代末發展底定為「(希臘文)羊皮紙筆記本」上的耶穌講論共筆——它的性質都從未改變,乃是一份基於「口傳」教導的複習筆記、僅在私下的小群範圍內流通。我們在比較探索「Q的消失 vs.四福音書留下」的,不可忽視的是它們的體裁/用途差異。參Richard Bauckham et al. (1998) The Gospels for All Christians: Rethinking The Gospel Audiences. Eerdmans
- 4. Stanton (2004), Albl (1999) 及 Harry Y. Gamble (1995). Books And Readers In The Early Church: A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 Texts. 是三本鑽研並回顧這個議題的深入學術作品。關於「口傳妥拉」抄寫筆記→ 耶穌講論共筆(Q)→ 二世紀基督徒全面以頁冊裝載聖經文學的因果演進,在專研此議題的幾位學者存在一致的結論共識。如 Stanton (2004), p.184 f.82 寫道: > ” If written collections of Scriptural excerpts existed among followers of Jesus even before Paul wrote I Thessalonians c. ad 50, they would have been in one of the forms of notebook referred to above. Since testimonia and Scriptural excerpts played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very earliest Christian communities, the familiar notebook or ‘page’ format used is likely to have been retained and developed as a form of codex for more substantial writings rather than the roll. … Albl and I seem to have reached the same conclusion independently.” 另 Irven Resnick (1992). "The Codex in Early Jewish and Christian Communities"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17, pp.1-17 的結論,也支持「頁冊」在基督教世界主流化的起步點,源於耶穌時代其門徒抄筆記的循例。 > Since the earliest disciples apprehended the person of Jesus especially through his unwritten words, which formed an oral tradition, it is possible that Jewish-Christians would have used the same form to record this oral tradition as the rabbinic community used to record its Oral Law without violating the ban against its publication ... [w]hile ...an entirely different psychology would have been at work ...[b]y the time the Church had become a largely gentile community-that is, by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second century-Christianity had disavowed the use of the roll for biblical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