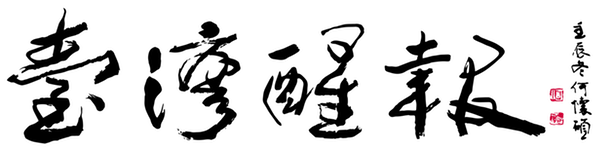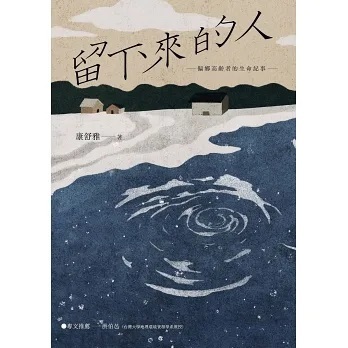
台西村,一個因環境抗爭與《南風》攝影集,而廣為人知的沿海小村。但是,檯面上的新聞,鮮少突出此地的高齡議題。在這樣的偏鄉,長者如何安老?作者身為都市成長的青年世代,反思自己與台西村的阿公阿媽,雖是血緣至親,卻像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
為了解這份差異從何而來,作者於碩士階段展開田野研究,試圖理解環境抗爭之外,台西村的高齡者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他們的日常生活是什麼模樣?
本書描繪的台西村高齡者,出生於1930、1940年代,自小從農,大部分只接受過數年小學教育。到了晚年,因台灣社會的劇烈變遷,他們難以再循傳統農耕社會的大家庭模式,將勞動責任交予下一代,也無法在子孫環繞下,安養天年。
台灣西部沿海一個偏僻小村裡,住著一群年事已高的海口人。
海口人出生於戰亂時代,自小從農,大部分只接受過數年小學教育,一輩子勞苦營生。身體成為他們摸索世界與理解社會的基礎,並據此建構起生活方式、人我互動及價值觀念。因為長時間投入勞動,他們與身周環境維繫著緊密關係,而著根的地方紮得既深且牢,更影響了他們對晚年生活安排的看法。
還留存在老家者
我的祖輩在此建厝,然至今還留存老家者,只有阿公、阿媽二人而已。他們二人雖是我展開碩士論文研究的起點,但在實際探訪村裡高齡者之前,我只是一名長年生活於台北、偶爾返鄉度暑假的孫女,平淡停留於祖孫關係所框限的相處經驗,並無密切互動,甚至沒有和同村人對話的印象。幼年時在阿公、阿媽教導下的台灣話,更漸漸被台北的都會氣質洗刷得七零八落。
在我的家族中,無論是留在老家的親人,或遠赴他鄉打拚的出外者,都盼望下一代在都市裡取得社會菁英的資格,未來過上不一樣的人生。在這種盼望下,我自小生活在物質豐裕無缺、毋須拚盡力氣生存的環境,浸潤在文字所架構起的體制中,系統性地學習特定的社會表達與各式標準。
這些在都會裡的生活經驗、學習成長,卻好像成為一道柵欄,隔開了我與家鄉。隨著我年紀漸大,日漸感到柵欄越築越高,好像阿公、阿媽那一輩人的標準、知識、表達,都和我有很大的差異,幾乎像是不同世界的人。
我不理解他們,也少有理解他們的機會,或許是因為這群人鮮少顯影於公共的視野中,也未曾在我熟悉的文字書籍裡現身。屬於那一世代、那一群人的集體記憶,存在於親密的口頭述說裡、存在於未患阿茲海默的腦海裡、存在於泛黃的老相片、也存在於田圳屋瓦的崎嶇紋理中,卻不存在於文字世界裡。即使有些故事在家族成員間流淌、傳承,在公共層面上卻鮮有聲息。仿如一株植物逕自在角落生長、開花與腐朽,而不為世界知曉。
故事發生在台西村
台西村高齡者的過往如何引領他們行至當下,乃至於當下立足之處所關聯的遲疑與未解,是我研究期間的焦點。越是深究,越感書寫成書的必要─他們的人生故事如同一面稜鏡,折射出台灣自日本殖民後期以來這七、八十年的農村轉變,包括那一世代的人們如何活過戰後的刻苦生活、城鄉移動如何發生、以及當代農村老化趨勢的具體景象。
故事發生的地點台西村,之於社會大眾而言,是萬千衰退農村的其中「之一」;許多人的長輩,也是高齡化趨勢底下的其中「之一」。
「之一」看似瑣碎平凡,是日復一日不斷經歷的日常,沒有特別之處,沒有足以令人聚焦的吸睛亮點,但事實上,「之一」代表著還有眾多千千萬萬個相似的案例,這些經驗因此超脫了個人,具有集體共享的意義。
凝視與書寫高齡者的日常,並非純粹的故事分享,而是政治性的行動。我想起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看法,他認為,研究者必須將日常生活作為一種問題意識來探討,也就是將日常「問題化」:假使現況還有改革的必要,則在當今世代中,已經不限於在政治、經濟等結構性的層面改革,而必須回歸人們的生活世界,因為改革涉及了在日常生活質性上的變動與改造。因此,深入理解常民的日常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微觀日常世界
本書延續這樣的關懷,希望透過建構起高齡者的微觀日常世界,描繪出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如何行過困頓的人生,並在晚年的變動中,如何調整生活秩序、如何轉換關係、如何在衝突與矛盾中掙扎並經歷調適,而他們的過去又如何奠定了根基,形塑了他們的信念、認同與價值觀,據以度過晚年。
這群留在家鄉的人,在此生長、安家、衰老、逝去,與移居他方的親人好友或遠或近地維繫不等的關係。我站在那方與彼端,凝視他們,叨絮著這些既平凡又特別的人物生平,零零碎碎蒐集起在時空甬道中碰撞所產生的對話、回聲與鳴響。作為一名投石者,希望在石子入水的這一瞬間,能夠激起漣漪,製造更多四濺聲響。
織補工多半凋零
雀仔人如其名,如小雀一樣鎮日忙活,勤快家務事、田事,還有各種雜工。她喜歡說話,有人的時候說,沒人的時候也說,話說得多又快、快又好,串串俚語,生動非凡。高齡八十有三的她,仍努力在生活裡填塞各種工作,時常告訴外地返鄉的子孫:「我才毋是閒人!規工攏咧捙拚!」
她的童年艱辛,那根深柢固的生存緊迫感,似乎跟著她一輩子。
雀仔總是不停做事,一刻也閒不下來。若有漁網可織補,她便不會午覺。像在和時間拚鬥,每一次都要在速度上追求超越。午後若補好四張網,她便欣喜滿足。雖然渾身疲憊,夜晚得拿舒筋霜揉一揉手腳,但肯定能一夜好眠。
時至今日,織補工多半凋零,像雀仔這樣的工人,村裡一隻手就數得完。台西村那間漁網織補工廠依舊存在,經營者已經從挺仔的父親頂仔,傳到頂仔的孫子一代。只是織補的工作,從以前棉線製成的漁網,改為由塑膠繩線穿成,亦有機具協助編製,業務也擴展出醃菜網、籃球網等各式網具。
偶有外地工廠慕名而來,對著雀仔說:「我揣真久,才揣著遮,聽講遮閣有人會曉補!」雀仔每回聽見此話,總是樂呵呵笑,既驕傲又大器地向對方表示:「若有網仔,就提來!」
於是網子一車又一車載來小小的三合院,每回都在宅院右側無人居住的廊下堆積如山。工廠主說:「有閒的時做,就好矣,我過一站仔才閣來提。」但雀仔總是在網子一載到的當口,便整日投入縫補漁網的作業,幾乎是不眠不休的架勢。據她的說法:「我人都閒閒,加補一張,就加趁一張的錢!」
渾然不覺時間流逝
雀仔的技術確實高超,工作時,手部動得飛快,穿線之間毫不滯留,身體餘部幾乎無甚動作,只是支撐。漁網上的經緯如工廠的生產線,一格一格以規律迅捷的節奏輪替。一張漁網平均一個小時能補完,雀仔一天最多能補七、八張。
除了隨日頭西斜、為躲避陽光而起身挪動位置,她整個下午就坐在一張有靠背的小凳子上,旁邊只有裝著剪刀、梭繩等工具的一個生鏽乖乖鐵桶,渾然不覺時間流逝。
織補雖不算耗力,長期坐著,也會坐出些職業病,對高齡的老人家來說,更是無可避免。雀仔在工作結束後,常常嚷嚷著手腕疼痛僵硬、背脊彎曲不直,甚至剛從椅子爬起來便頭昏目眩,搖搖晃晃,快要跌倒。
兒孫見到雀仔如此,總是力阻,要她不要再接織補工作了。但她沒有理會兒孫意見,只轉頭向工廠主討了更高的價格。停滯數十年的價格終於在人才凋零的現時,不得不有所更動:從一張網三十五元,漲到一張網七十五元。
勞動價值的體現
以兒孫角度來看,雀仔根本不需要花那麼長的時間,把自己搞得渾身痠痛,去賺取那點微薄利潤。確實,以市場價值衡量,織補工作的投資報酬率甚低,沒有賺頭。在一般人眼中,這只是被「剩下來」的工作。但對於高齡者來說,這項工作所涵括的意義卻遠不止於此。
金錢收益雖是雀仔的動力來源,但織補工作所牽連的時間、體力投入與產出回饋,才是她能夠持續日常生活的原因。能夠從事織補工作,是一種勞動價值的體現,不僅替代了因為不去田間工作而空下來的大把時間,也是雀仔證明自己仍具有生產力的方式,她可以從中感到付出與收穫的成就感。
二〇二〇年夏天,兩人的小女兒回鄉,臨走前,雀仔忙著打包蔬菜食物,進進出出,就在曬穀場上與小女兒對撞,直接往後仰倒在地。匆忙送醫後,開始了漫長的療養。
最初幾個月,她得仰賴旁人幫忙洗澡、換衣服、上廁所,幾乎無法出門。
整日都躺在椅子上
雀仔的復原過程,牽動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質配置改換,以及她與子女的關係。雀仔要定時就醫,必須有人攙扶,也得靠人開車載送。小女兒在雀仔傷後初期,幾乎每週都留鄉照顧父母。她是個勤於照顧環境的人,自從接手家務工作,就開始整頓過去因老人家無力打理而顯凌亂壞損的屋宅內部:買了一台新的洗衣機,將雀仔平常習慣歇息的座椅鋪上軟綿綿的坐墊,讓她不必起身移動,而能整日安歇於此;同時也清掃廚房內外,將雜物收拾妥當,以免造成路障,又在昏暗廊上安裝一盞感應式照明燈,防止晚間看不清路再有跌跤。
這樣過了幾個月,雀仔頭部的傷已然好轉,手骨卻仍使不上力,怎樣都無法像傷前活動自如。看了漢醫,也持續復健,卻似乎成效甚微。她常一臉愁苦,無奈嘆息:「就按呢矣啦。」
因為受傷,雀仔忙碌充實的日子,倏忽被抽取一空。因為活動不便,她整日都躺在椅子上,有時暗自神傷,漸漸不想進食,也不願鄰居朋友來訪,說自己這樣「袂用得見人」。家人輪番陪著她說話,她的精神卻不見好轉。
傷後日常是無常
傷後一年,雀仔終於能夠走動,單手提得起鍋鏟,也能拜訪鄰人。雖然手部仍然無力,但臉上笑容漸多。原以為情況就要好轉,誰知旋即遇上嚴重疫情,鄉人遍地恐慌,人人緊閉家門,連院落也不願踏出。往常到鄰家串門子的習慣被迫終止,子孫千叮嚀萬囑咐,要自家長輩出外必戴口罩,沒事不要出門。
受傷後,雀仔不再去田裡,因為腿骨漸漸無力,連騎腳踏車都喊疼,甚少外出走動。雀仔只能盼望著她的漁網工作。可是近年補網的工作量也少了,她無聊的時間越來越多。因為行動能力有限,往往只能坐在廳裡放空,偶爾拿起手機、點開YouTube,喃喃說著「我欲看囡仔」,一邊這樣說、一邊伸出食指滑動螢幕。這是她的兒女教了多次以後她總算學會的成果。就算不識字,也能看影片消遣。
不能再勞動
她一向喜愛年齡稚幼的孩子,他們天真無邪的可愛模樣,總會讓她露出開懷又溫柔的表情。
後輩總催著雀仔要多走、多動、多吃東西,盡量心情樂觀些、不要想東想西。可是對雀仔而言,投入勞動的身體條件如今越來越嚴苛,每每努力去一趟菜園回來,腿骨就痠疼不止。她常常一邊推著藥膏、一邊哀哀抱怨著:「做死,這跤腿是按怎、我無路用矣。」幾次以後,雀仔本人與旁觀的家屬,才在不同的時間點漸漸明白,她已經不能再勞動了。
出於對健康的顧慮,家人易視她為「囡仔款(孩子樣)」,她自己也容易如此自嘲。不只是雀仔,整個社會環境在各種與高齡者的互動之間,時常有意無意顯現出這種態度─高齡者是需要有人看顧、需要被檢視行為的對象。原因很複雜,中間總是投射著家人的盼望、主流社會對於「健康」定義的標準,以及對「老年」的隱約恐懼。
一方面,兒孫希望看見高齡者妙語如珠的活潑樣子,希望他能保有成人的健康活力;同時,期望卻也如同迷霧,讓人看不清高齡者的真實情境。高齡者的真實需求,常常經歷一番拉鋸、抗議與行動展示、才能顯現,從而才有機會與家人的諸般期待達成平衡。
家屬對雀仔懷抱著能夠盡量維持生活自理的期待。但是,生活自理的範圍如何拿捏,在實際情境中卻是充滿困難的進進退退─當她的體能好一些,就能多做點事;體能差時,一切幾乎癱瘓。
旁觀者究竟是要盡量維持她對生活的責任,讓她緩慢地為植物澆水、有力氣時為家人煮飯;還是相信已經到了不可逆的階段,轉而接手一切,讓老人家靜養?對雀仔來說,在她精神恍惚,難以應答時,她又如何表達自己?
這些困難,都不是發生的當下能夠決定的。家屬只有仰賴著對她平日行為與個性的知悉,在照顧她與放手之間慢慢摸索著適切的作法。 (章文/輯)
《留下來的人:偏鄉高齡者的生命紀事》
作者:康舒雅(曾獲台灣社會學會田野工作獎作家)
出版社:游擊文化